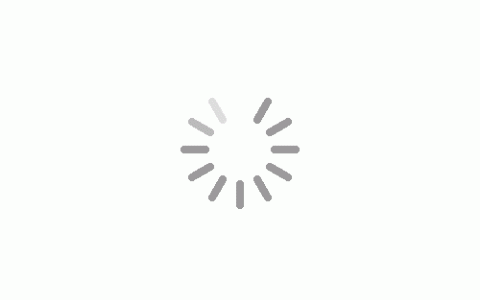近日,安徽省前城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前城股份)法定代表人孙增文在微博连发多条控诉材料,引起外界的关注。
根据微博内容显示,孙增文实名指控合肥兴泰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兴泰集团)前任董事长程儒林,以及商人蒋士平通过相关手段,取得了前城公司旗下子公司名下价值2.2亿元的地产项目,也因此导致前城股份公司面临破产的局面。
据孙增文介绍称,前城股份是一家有着近十年的民营房地产开发企业,其因为合肥一块住宅项目与兴泰金融控股集团展开合作,并在时任董事长程儒林介绍下认识了华亿投资有限公司(下称华亿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士平。在孙增文看来,与他们的相识,为其公司随后遭遇的一系列变故埋下了伏笔。
根据孙增文提供的材料显示,蒋士平等人先以6000多万元借款为由对当时孙增文持有的宿州市新里程置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里程)项目进行投资。随后在孙增文安徽亳州项目出现问题之时,蒋士平以保护该项目为由让其签订一份“股权代持协议”,然而就是这份所谓的协议,让华亿公司最终以6000多万元借款成功获取了价值2.2亿元项目。
在失去新里程股权和项目所有权后,孙增文也一直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其先后上诉至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人民法院和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但一审和二审均以失败告终。无奈之下,孙增文通过微博进行实名控诉,以此希望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6000多万借款套取2.2亿元资产?
关于前城股份公司的案件要追溯至2017年,当时,前城股份与兴泰集团在合肥肥东114亩住宅项目展开合作,孙增文因此结识了程儒林。
随后,在2018年2月,程儒林主动提出以融资的方式把前城股份公司在合肥合作化南路7号的132亩土地抵押给兴泰集团旗下公司–兴泰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下称兴泰公司)贷款1亿元资金用于孙增文在亳州的项目,并趁机介绍华亿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士平给孙增文认识,蒋士平也因此作为本次1亿元贷款的担保人。
据孙增文称,由于长期与程儒林、蒋士平相处,并且亲身经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因此他认为蒋士平人品非常可靠,因而在后续的往来中对蒋士平深信不疑。
“蒋士平的入局,正是后来一切的开始。”孙增文事后回忆说。程儒林将蒋士平引荐给孙增文认识后,透露蒋士平手中持有六千多万元,提议将这笔钱以借款的名义给孙增文使用。处于对流动资金的需求,孙增文同意了此事,随后蒋士平便以华亿公司的名义多次合计向前城股份公司转账六千多万元。
然而这笔借款没过多久,在2018年8月18日,程儒林以蒋士平借给前城股份的六千多万元不收利息为由,要求前城股份把新里程公司开发项目的30%股份转让给蒋士平。对此,孙增文介绍称,因前城公司在兴泰集团有1亿元贷款,所以他同意了这个提议,因此在当天(8月18日)签订了《股权代持协议》,将新里程公司30%股权转让给蒋士平。
根据《股权代持协议》显示,甲方为蒋士平,乙方为前城股份,丙方为宿州市新里程置业有限公司。协议具体内容是:双方为了合作开发位于安徽省宿州市韩池子南路与淮河东路交叉口西北角“前城御府”的房地产开发事宜,共同投资丙方,股权比例为3:7,甲方因股东之间合作事宜,暂时不便处理公司事务,便将所持有的新里程公司股权委托乙方前城股份代持。双方确认彼此之间是股权代持关系,乙方前城股份自愿接受甲方蒋士平的委托。
值得注意的是,新里程公司开发项目,是前城股份在2017通过协议收购的方式获得。具体情况是:2017年7月2日,前城股份与淮北市顺龙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下称顺龙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前城股份通过协议收购顺龙公司持有的宿州市新里程置业有限责任公司95%的股权,并代持5%股权。根据合同约定,前城股份陆续支付了8499万元的对价(其中4684万元代为垫付给政府)。基于这一交易,顺龙公司将新里程公司100%的股权转让给了前城股份,这也使的前城股份获得了新里程公司的全部开发权益。
随着代持协议的签订,孙增文面临的麻烦也接踵而至。在2018年11月,前城股份因投资亳州房地产项目陷入债务纠纷和诉讼,出现资金困难,施工单位申请安徽省亳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财产保全裁定冻结前城股份持有新里程公司的100%股权。此时,蒋士平借机提出,为规避新里程公司财产权益被司法冻结的风险,可由前城股份将所拥有的新里程公司100%质押的股权全部释放转移至蒋士平名下的华亿公司。
同时,蒋士平和顺龙公司负责人张百其,利用前城股份项目可能被查封及债务临近违约、与合作方产生矛盾的危困风险,让前城股份与华亿公司、顺龙公司及新里程公司共同签订一份《补充协议》。
对于这份补充协议,孙增文回忆称“这实际上是有意而为之的行为。”然而,正是这份协议,让前城股份彻底出局。据《补充协议》显示,前城股份按照《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支付的全部款项均视为华亿公司实际支付,华亿公司也无需就获得原合同权利义务另外支付任何对价,这也意味着华亿公司获得了新里程公司的全部股权,并且持有旗下项目的开发权。
换言之,蒋士平凭借6000多万元的借款以华亿公司名义受让了前城股份持有新里程公司70%股权(市场价值2.2亿元)。这不仅导致前城股份在《股权转让协议》中享有的实际持有的新里程公司的股权被上述两家公司共同瓜分,还造成前城股份直接损失约1.04亿元,包括此前与顺龙公司之间的交易对价8499万、项目前期各项支出1865万。
在《补充协议》签订后,华亿公司、顺龙公司于2019年1月4日通过工商变更登记瓜分了新里程公司股权,其中华亿公司获得70%的股权份额,顺龙公司获得30%的股权份额。
需要说明的是,按照最初的前城股份与顺龙公司协议约定,顺龙公司理应仅持有新里程公司5%的股份。显然,顺龙公司和华亿公司在新里程公司的股权问题上达成了某种共识。
一日签订两份截然不同的协议?
实际上,《补充协议》背后的故事远不止表面看上去的这么简单。“这份《补充协议》就是假协议。”孙增文在接受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采访时指出,“这份协议签订的时间有问题,本来是2018年12月19日签署的合同,但《补充协议》上的签署时间却为2018年8月18日,即与《股权代持协议》同一天。”
诚如孙增文所说,他不可能一天之内作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决定。一份是孙增文帮蒋士平代持其手中新里程公司30%的股份,另一份则是将新里程公司无偿转让给蒋士平所属的华亿公司。
至于为何蒋士平要将两份签在同一天?据孙增文事后回忆,当日(2018年12月19日)被迫签订《补充协议》的时候并没有签订合同时间,而2018年8月18日这个时间是他们之后补上去的,“两份协议一定要签在同一天,一方面是为了营造假象,让外界认为第一份《股权代持协议》从未存在过,而第二份补充协议才是真正的合同;另一方面,通过将时间统一为2018年8月18日,能够让新里程公司法定代表人张百其更好地为该项目在当日完全转让给蒋士平进行佐证。倘若补充协议的合同签在12月,中间相差4个月的时间,必然会让补充协议的真实性受到质疑。”孙增文介绍称。
在蒋士平拿到新里程公司的股权后,在2019年1月和3月,前城股份一直要求蒋士平返还新里程公司70%股权,但都遭到拒绝。不仅如此,蒋士平还采用相关手段迫使原先已经进场施工的新里程项目的承包商湖南省第五工程有限公司(下称湖南五建)作废原施工合同,并遣散施工人员。
双方在施工现场的纠纷,也在2018年7月被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做了专题报道:事发宿州!两家建筑商争抢一个工地 背后真相究竟如何?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湖南五建的合作,要从2018年6月7日说起,彼时新里程公司的股权尚未被华亿公司等企业获取,前城股份代表新里程公司与湖南五建签订了《宿州前城御府项目施工总承包合同》,合同约定由湖南五建承包新里程的项目施工。然而,在华亿公司受让新里程公司的权利、义务后,在华亿公司主张下,新里程公司与其他公司重新签订了施工合同,对湖南五建也造成了经济损失。
也因此,湖南五建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新里程公司赔偿相关损失费以及赔偿违约金等。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湖南五建曾于2019年5月24日向法院提出诉前保全申请,请求查封新里程公司名下土地项目使用权,法院也予以同意。
一方面,蒋士平控制的新里程公司与湖南五建有重大诉讼,新里程公司名下土地项目被查封。另一方面,前文提及,前城股份因亳州项目被案外人冻结了名下宿州前城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时还面临着与兴泰集团之间1亿元外债的还款压力,企业经营已面临绝境。前城股份无力偿还这笔款项,蒋士平为该笔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被兴泰案件强行执行1亿元。
需要说明的是,在股东及公司均涉及重大诉讼的情况下,按照相关规定,蒋士平本不应获得金融支持。然而,兴泰集团却向蒋士平提供了7500万元的融资,用于宿州109亩地产项目的开发。
此外,孙增文还介绍称,他们对前城股份的手段还不仅仅于此。为了让前城股份加速衰落,他们随后开始快速收贷,因前城公司无力偿还该笔款项,他们将其抵押担保的位于合肥合作化南路7号的132亩土地总价值5亿元(政府收购价)进行查封,远超案件标的价格。最终,合肥合作化南路7号的132亩土地以2亿多元的低价被拍卖,而宿州109亩地产项目开发完成后更是获利数亿元。
维权困难重重?
事情发生后,前城公司一直在通过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权益。
为此,前城公司于2020年1月20日诉至法院,请求撤销前城公司与华亿公司、顺龙公司、案外人宿州市新里程公司签订的《补充协议》。此案由合肥高新区人民法院审理,经过1年多的审理后,最终于2021年7月29日下发一审判决结果。
根据合肥高新区人民法院判决书显示,前城公司主张:华亿公司及其负责人蒋士平拉拢、串通顺龙公司及其负责人张百其,趁前城公司项目面临可能被查封、债务临近违约以及与合作方产生矛盾的危困之际,诱使前城公司签订了《补充协议》。该协议致使前城公司实际持有的新里程公司95%股权被华亿公司和顺龙公司无偿瓜分,各方的意思表示均为虚假,且严重违反公平原则。
同时,前城公司提供《补充协议》、《股权代持协议书》、银行转账记录及多次微信聊天记录,证明协议签订目的为规避法律风险,并非真实意思表示,两被告意图非法侵占项目权益;提供《融资租赁合同》以及蒋士平与孙增文关于兴泰集团担保借款债务问题的聊天记录截图等,证明案涉《补充协议》签订前后,前城公司正遭受其他项目土地被查封、债务到期等危困状况。
而华亿公司辩称,前城公司在签署《补充协议》时并不存在危急状态或缺乏判断能力的情形,协议的签署和履行也未造成利益不平衡。此外,华亿公司否认各方存在通谋行为,坚称《补充协议》为合法有效。同时,顺龙公司则表示,前城公司因财务问题履约能力缺失违约后,告知顺龙公司前期投资来自华亿公司,并请求顺龙公司与华亿公司继续合作,这才签订了《补充协议》。之后,华亿公司主导项目启动总体是顺利的,在项目启动后,已经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进行项目建设,现前城公司再行主张撤销三方《补充协议》已经事实上不可能。
根据一审法院查明,《补充协议》的实际签署时间是2018年12月19日。此时间段,前城公司已经面临因大量债务资产被司法查封,为了避免新里程公司资产被查封、冻结,才签订上述《补充协议》。但法院最终认定前城公司提出的《补充协议》中“无偿转让股权”显失公平的理由不成立,且不能得出其签订《补充协议》时基本丧失判断能力,并驳回前城公司的诉讼请求。
在一审法院诉求被驳回后,前城公司因不服判决结果,向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前城公司的一审诉讼请求,该案件于2021年11月22日予以受理,并于2021年12月10下发二审判决结果。
在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书中,前城公司提出:一审法院未查清华亿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士平委托前城公司代持新里程公司股份的事实;《补充协议》内容如此草率,印证了前城公司所称为了避免新里程公司资产被司法查封的陈述属实。
然而,华亿公司在二审则辩称,前城公司所述的危困状态是由于两起债务纠纷,一是与宏渠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之间的债务纠纷,二是与兴泰公司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兴泰公司贷款到期日为2019年3月15日,且华亿公司法定代表人蒋士平为该笔贷款提供了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这些都是正常的经营行为,且并不发生在签约时,并不能证明其客观上处于危困、急迫状态、缺乏判断能力。
最终,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前城公司正常经营风险不足以判定其在签署《补充协议》时丧失基本判断力,华亿公司基于实际出资签订《补充协议》系正常商业交易行为,不存在显失公平等”为由,再次驳回上诉。
两次起诉,两次被驳回,似乎事情的结局已尘埃落定,但是孙增文表示自己并未放弃,“尽管遭遇重重困难,但我仍将通过法律等方式维护自己的利益,继续为自己的公司讨回公道。”

文章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负。转载请注明出处:远视互动